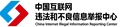充滿剛健氣息的另一種苦難敘事 ——讀寧夏青年作家馬駿散文集《青白石階》
“如若不是經(jīng)由這些文字,,誰會注意到,,西海固小城路邊的一排青白石階上,曾經(jīng)久久癱坐過一個叫馬駿的無法站立的孩子,。與這片土地上慣常被言說的干涸與貧瘠相比,,馬駿與生俱來的苦難更多源于刻骨的孤寂、彷徨與被放逐,。而那青石臺階,,成為他穿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眺望世界的唯一洞口,。在靜如深潭,、漫無邊垠的守候里,常人鮮有覺察的那么多善良,、溫潤的生命細(xì)節(jié),,被敏感的他近乎極致地扣藏下來,沉積發(fā)酵,,散發(fā)著藥劑般的微苦,,終有一日化為文學(xué)。于是,,他完成了醫(yī)學(xué)難以企及的治愈,,讓自己的靈魂勇毅地站立起來。他的文字如一道剛剛鑿?fù)ㄋ淼赖墓?,微渺,,但堅決、強韌,,照亮茫如旱海的前定,。”這是我為回族青年作家馬駿新出版的散文集《青白石階》所寫的封底推薦文字。
2020年,,我在《民族文學(xué)》做編輯時遇見馬駿的散文,,當(dāng)時恰在約組以“五四運動”領(lǐng)袖馬駿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故而對眼前這位晚出生整一百年的同名小弟有幾分親切,。方得知,,1995年生于寧夏西吉的馬駿自幼患脊髓性肌萎縮,只能坐在輪椅上寫作,。我很敬重這樣的寫作,,但并不想因作者特殊的身份才去推舉,而是想還原成同健康人一樣的寫作標(biāo)準(zhǔn)去對待,,便對一些尚顯青澀之處提出修改意見,。面對密集拋來的幾十條60秒“碎碎念”,微信那頭的馬駿珍惜而懇切地傾聽每一句,,像是西海固的莊稼如饑似渴地吸納著雨水,。他居然真把先前稿件推翻,,重寫了一遍又一遍。我感到他心底藏有天然的悲觀,,總茫然于是否還要堅持下去,,但同時在行動上又從未松懈,反有股誓不罷休的“狠勁兒”,。正因看到這種可貴的堅持,,我在轉(zhuǎn)向新的職業(yè)后仍一如既往關(guān)注著他,陸續(xù)在《六盤山》《朔方》《民族文學(xué)》等刊物見到他的新作,。他的拔節(jié)之聲內(nèi)斂而響亮,。
對西海固文學(xué)而言,《青白石階》一書可能是一種新異精神氣質(zhì)的注入,。許多人對這片土地的理解難以僭越苦難這類關(guān)鍵詞,,這主要由于極端嚴(yán)峻的自然條件給人們生活造成的歷史負(fù)累。及至馬駿這一代,,生存上的困厄局面早已有了本質(zhì)改觀,,但馬駿在身體和精神上經(jīng)歷的獨有苦痛又較之常人沉重許多。在同名散文《青白石階》中,,他記述了身為“只能略微移動且有思想的植物人”長久坐在青白石階上的蝕骨記憶,,沒有玩伴的自己只能把手掌擦在水泥上感知細(xì)胞彈動,讓螞蟻爬上手背抵御孤獨,。一輛踏板車的出現(xiàn)使他有了結(jié)識同伴的“本錢”,,然而卻因車被撞壞再次失去同伴。多年后,,那輛落滿灰塵的踏板車被家人棄為廢品,,青白石階也在街道改造中被拆除。在敘事層面,,這段事體并無復(fù)雜面向,,甚至有些簡易而粗略,然而它仍成為全書給我留下最深烙印的作品,。在眾生眼中,,一方石階或許是無足輕重的,但對馬駿而言卻是他的“地壇”,,是他與世界對話的原點,。他那樣渴望逃離石階,向遠(yuǎn)方自在游弋,,然而我并未在他的表述中看到任何對這個限制了他自由的石階的怨艾,,相反卻有充滿溫情的懷戀與不舍,以至當(dāng)它被鏟碎的一刻,“隱約有個衣衫襤褸的男孩告訴我,,你再看看這青白石階,,再好好看看,這也是你最后一次看到青白石階了”,。這深海般的善意淹沒了軀體的無助,、離群的失落,使枯燥冰冷的青白石階生成為一個與傳統(tǒng)苦難敘事相對峙的頗有力量感的美學(xué)意象,。
在隨后的篇章中,作者著重敘寫“上學(xué)路上”的艱難史:無法入學(xué)的自己仍只能坐在石階上等待妹妹和同伴放學(xué),,為了讓路過的同伴看到自己也有書讀,,他舉起鄰居家淘汰的課本,捍衛(wèi)最低微的自尊,,不想竟把書拿倒了,,反招致嘲笑,于是便有了《孔乙己》般令人心疼的描述,,“西斜的稀薄陽光里蕩漾著他們遠(yuǎn)去的笑聲”,。后來,在母親的堅持下,,作者終于得以入學(xué),,每天送他上學(xué)的父親成了他的“雙腿”:“他一手扶住我的腰,一手抵住我的前胸,,掌握好平衡,,微微蹲下身子,將我架上肩膀,,右手?jǐn)r住我的雙腿,,左手拎起書包,將我身體的平衡點從大梁車移動到他身上……”類似一連串動詞也曾出現(xiàn)在《背影》中,,月臺送別的短暫一瞬成為深沉父愛的經(jīng)典形象影響百年,;然而須知,這樣的動詞對馬駿而言,,卻是無限疊加在他從小學(xué)至高中畢業(yè)前的日日年年,。更令人疼惜的是,馬駿的弟弟出生后也患有先天性疾病,,父親再次成為弟弟的“雙腿”,,進入新的痛苦輪回。如果沒有人把殘障家庭這些深潛骨髓的疼痛記憶復(fù)原出來,,我們很難深入理解弱勢群落肌理深處的生命難以承受之重,。是馬駿把這個世界打開了,亮出目不所及的角落里隱藏的人性堅韌與強悍。
或許基于經(jīng)歷相仿,,有論者將馬駿比作“西海固新時代的小史鐵生”,,不過就實際經(jīng)受的困難程度而言,馬駿可能更有“資本”將所謂苦難敘事進行到底,。他不僅是雙腿殘疾,,而且因肌無力居然伸手舉筆都很奢侈,很難想象他是如何完成寫作的呢,?加之貧寒的家境僅靠開一間小雜貨鋪為生,,治療成為遙遠(yuǎn)奢望,本已考上大學(xué)卻無法就讀,,因出行不便錯失外出進修機會,。霜刃一次次剜割在稚嫩的心上,但馬駿的文學(xué)敘事中即便寫到疾患與遭遇也只是客觀冷靜地陳述,,好像把握著某種尺度,,有意拒絕著可能的展覽苦難的傾向。在他的講述中,,我沒有讀到劇痛,、絕望甚至哀愁的深淵,而是自始至終被文字中涌動出來的一股永不屈服,、永遠(yuǎn)向上尋找希冀與尊嚴(yán)的“自助”力量所俘獲,。他是怎樣做到吞咽下靈魂的永夜,吐納出來的全是光明與美好的呢,?或許這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身體敘事”——身體不再成為獵奇與消費的資本,,而是滿盈著如同青白石階那般清清白白的精神,如同向日葵那般筆直,、剛健,、溫暖的力量。這是馬駿文字雖顯質(zhì)樸,,卻足以攫動人心,、使人久久不能釋懷的根性魅力所在,也是他為西海固傳統(tǒng)苦難敘事貢獻出來的富于啟示意義的新經(jīng)驗,。
今年一月,,我結(jié)束了在甘肅積石山地震災(zāi)區(qū)的志愿采訪,趕到寧夏固原參加《青白石階》研討會,。行走在災(zāi)區(qū)一個個破碎的村落時我就在想:文學(xué)究竟為何而存在,?是為著創(chuàng)造和傳遞人類深邃思想,是為著銘記歷史與表達(dá)情感,,還是有什么更高遠(yuǎn)莫測的追求,?但我堅信,一定有一種文學(xué)是與生俱來為著撫慰人心而誕生的,。馬駿的文學(xué)就是這一種,,它并不只是基于個體傾吐的需要,而是更多呈現(xiàn)出一種利他品質(zhì)——如同史鐵生孵化了馬駿一樣,,馬駿的文字也可以變成一束光,,照亮更多危困之中的靈魂,讓那些地震災(zāi)區(qū)中失去家園的孩子,,清苦的,、病患的、孱弱的,、失去信心的人們看到,,一個可能比他們更艱難的青年,就是如此真實地在文學(xué)之光的燭照下勇敢站了起來,!甚至倘如,這世上一切深陷困境的人們都能像馬駿一樣用文學(xué)治愈自己,,與這個世界和解,,該多么好。(作者: 石彥偉)
相關(guān)新聞
-
楊風(fēng)軍散文集《生前身后》研討會在市圖書館舉行
[2025-04-26] -
非遺丨執(zhí)著從藝路 巧手織錦繡
[2025-04-23] -
近100幅藝術(shù)作品展現(xiàn)多彩固原畫卷
[2025-04-23] -
書香為伴 |《西海固情節(jié)》
[2025-04-18] -
講述 | 那一年 那個班 那一程
[2025-04-18] -
口弦丨苦苦菜
[2025-04-17] -
口弦丨兄弟情長 往昔難忘
[2025-04-17] -
口弦丨鄉(xiāng)土情撫人心
[2025-04-17] -
口弦丨春來第一哨
[2025-04-17] -
口弦丨古稀歲月積天珍——書于何富貴新作《蕭關(guān)杏語》出版之際
[2025-04-17]